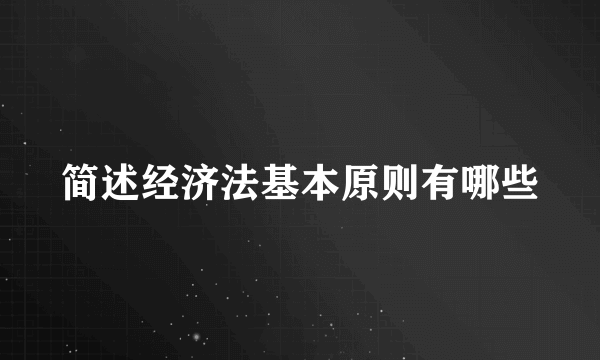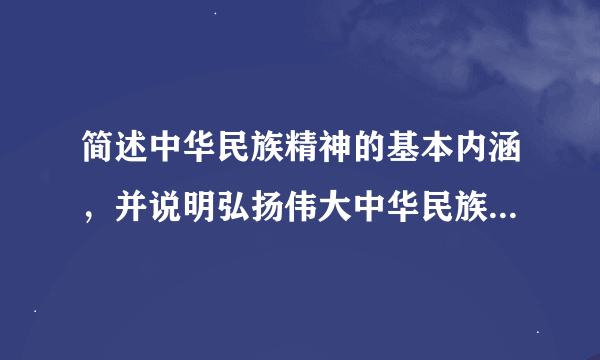简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明晰的过程,这也与它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建党之初对联省自治的否定;二是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通过联邦制这一国家结构形式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即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或“中华苏维埃联邦”;三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采纳,决定建立单一制的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否定武人割据式的联省自治 在民国初年关于联邦制的沸沸扬扬的争论中,虽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先驱人物如陈独秀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整体上直接介入这场争论。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对联邦制联省自治与中国国情予以高度重视。 1922年,针对如火如荼的联省自治运动,中国共产党认为,“不违反民主主义的联省自治,是由民主派执政的自治省联合起来,组织联省政府,来讨平非民主的军阀政府,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结果仍是一种民主主义对于封建制度战争的形式;绝不是依照现状的各省联合———联省自治的政府和北京政府脱离就算完事,因为这乃是联督自治而不是联省自治;更不是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几个封建式的军阀就可以冒称联省自治的,因为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算是明目张胆地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使造成一班武人割据的诸侯,哪里能够解决时局”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联邦制(联省自治)的赞成或反对意见,但却对以武人割据为基础的联省自治予以根本否定。在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针对当时出现的西南联省自治,中国共产党揭露了这种自治形式下的“联督自保”的实质,并指出,“主张此说者,不是失意政客观欲挟西南为奇货,以达其总裁头衔及分赃会议的欲望;便是贪鄙腐儒欲据此以为拥黎地步而已”。这与其说是对联省自治的否定,还不如说是对武人割据的否定。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应该反对军阀的分治主张,而赞成资产阶级的国民统一运动,并促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互相结合,而极力反对其互相分裂或与军阀合作……” 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或“中华苏维埃联邦” 与介入联邦制争论的各派政治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对联邦制的认识主要是与它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联邦制的主张,并将建立联邦制作为其奋斗目标:“……(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列宁在为1920年6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中国共产党二大所确立的上述奋斗目标正是依据这一思想所提出的第一个用联邦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方案。中国共产党提出以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实质上体现了对弱小民族及其平等地位与权利的尊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建立联邦制国家,通过联邦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1934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该法规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国境内各民族订立组织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条约”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项权力。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方针,“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同时决议还提出,在蒙、回、藏等民族“成立了独立国家之后,则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他们自愿的原则,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联邦”。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重要纲领,也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政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政府虽然继续主张联邦制,主张通过联邦制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但在其有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文件中则主要使用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提法。1938年10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不提联邦制,而是提“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宣布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阐述的民族政策,即“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尽管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很少提及联邦制,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这一主张。1946年1月16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草案中有一些具有明显的联邦性质的条款,如“地方自治”部分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省得自订省宪,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但在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已将这一条款改为,“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之措施,但省、县所颁之法规,不得与中央法令相抵触”。其中的变化虽然只是措辞上的细微的变化,如“省宪”这一颇具联邦色彩的概念在《和平建国纲领》中已不再出现,但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的态度已开始发生转变。 单一制的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汉族与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或者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因而将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或者将“中华民族”视同“中国境内各民族”进而将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视作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抗日战争中,各民族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威胁和共御外侮、保卫国家的共同的斗争经历,使各民族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并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及时洞察了这一现象,进而获得了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因而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政府的文献中,“中华民族”已不仅指汉族,还包括满、蒙、回、藏、苗、瑶等民族。“这种新的认识和解释不仅构成‘中国境内各民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这一主张的逻辑前提,而且构成革命获得胜利后建立单一制的统一的共和国这一决策的主要的理论依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主持中共中央民族工作的李维汉提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建议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建议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采纳。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它是“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这是其一。其二,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从此,建立单一制的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它不一定面面俱到,但应该视角独特它未必百分之百正确,但或许能给人启迪它也许给不出答案,但能拓展人的思考空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共识,也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和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政策。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问题的关注从内容到主张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关注始于建党之初中国社会的联省自治运动,但其后不久便将这种关注与中国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远不是一种随意的联想,而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客观认识和对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联邦制的整合功能的准确认识。在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与实行联邦制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的“以联邦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转向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框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是对中国国情基本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又是趋近于对于联邦制的本质认识的结果:在中国,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并在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生活经历中成为统一国族(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同时,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只集中分布于局部地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地域基础这一使民族因素对国家结构形式产生影响的重要中介。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事实,加之中国现实的民族状况(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各少数民族的地域分布等),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实行以民族为基础的联邦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却为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巩固国家统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