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的艺术读后感1500,不要太和网上一样。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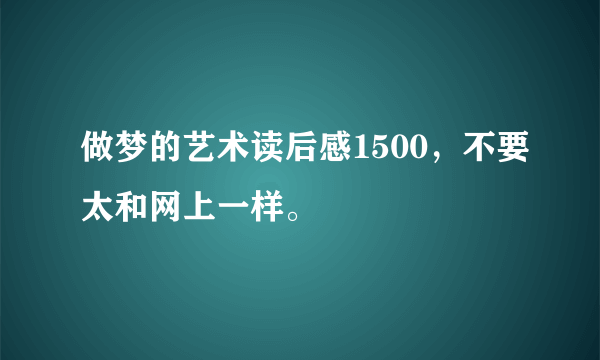
一切皆是能量,整个宇宙都是能量。 唐望说他们最重要的成就是知觉到事物的能量本质,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成了巫术(sorcery)的基本前提。现在,巫士经过毕生的纪律训练,能够得到知觉事物本质的能力,他们将这种能力称为“看见”。 “能够知觉事物的能量本质是什么意思?”有次我问唐望。 “这表示你能直接知觉到能量。”他回答,“能够分离知觉的社会化部分,便可以知觉到一切事物的根本。我们所知觉的一切都是能量,但由于我们无法直接知觉能量,使我们的知觉定型配合一种模式,而这个模式便是知觉的社会化部分,这是你必须分离的。”“为什么我必须分离它”“因为它故意缩减我们的知觉,使我们相信我们知觉所处的这个模式便是一切,我相信现在如果你想生存,你的知觉必须要从它的社会化根本上有所改变。”“确信这个世界是由固体的事物构成的,我称之为社会化根本。因为所有的人都用极大的努力来使我们如此地知觉世界。”“我是说这个世界先是能量的世界,然后才是物体的世界。所以,如果我们不从这世界是能量的前提开始,我们便永远无法直接知觉能量,我们总是会停留在你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感官上的确信:物体是坚硬的。”他们说宇宙的本质就像无数闪亮的白丝由各种方向射入永恒,这些明亮的纤维本身是一种知觉,是人类的心灵所无法了解的。 “看见”了宇宙的本质之后,古典巫士继续去“看见”人类的能量本质,唐望说他们把人类形容为明亮的像巨大的蛋的形状,他们称之为明晰之蛋。 在唐望的教导中,他曾一再提到并说明他认为是古典巫士最重要的发现,他称之为人类明晰球体中的关键特征:一处极明亮的圆点,像一只网球般大小,永远嵌在明晰球体内部,表面平贴,大约在人类右肩骨二尺之后。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描述时很难想象。唐望解释说明晰球体比人体要大很多,而那亮点是这个能量球体的一部分,位置约在肩膀的高度,离背部一臂之遥。他说过去的巫士在“看见了这个亮点的功能之后,把它称为集合点(Assemblage Point)。”“集合点的功能是什么?”我问。 “它使我们能够知觉,”他回答,“过去的巫士看见人类的知觉集合在那一点上,看见所有的生物都有这样的亮点,他们归纳知觉必然都发生在那点上,不管以何种方式。”最后,他们看到两件事:第一,人类的集合点能够脱离他们原来的位置。第二,当集合点是在原来的位置时,知觉似乎是正常的,这可从观察对象的行为方式来判断;但当集合点不是在平常的位置上时,从观察对象不寻常的行为可以证明他们的意识状态改变了,他们以不寻常的方式知觉。 人类的集合点借着集中光亮于穿过集合点的宇宙能量纤维上,自动而无计划地把这些纤维集合成一个对世界的稳定知觉。 古代巫士“看见”小孩的集合点时常浮动着,仿佛有暗流在推动,能自由改变位置。因此他们认为集合点的习惯位置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习惯造成的。他们同时“看见”只有成人的集合点固定在同一位置上,他们推论集合点所在的特定位置造成了特定的知觉方式,经过使用,这特定的知觉方式成为诠释感官讯息的系统。 唐望指出,由于我们被迫出生在这系统中,从出生时我们便不可避免地努力调整知觉来配合这系统的要求。这系统一辈子统治着我们。古代巫士非常确信要使平常人转变成巫士的话,就必须要反抗这系统,直接去知觉能量。死的生物上完全看不出一点集合点的痕迹。集合点与它的光环是生命与意识的记号,古典的巫士得到必然的结论,意识以及知觉和集合点及其光环有密切的关系。 当集合点被移动到不同的位置时,无数新的明亮能量纤维会集合在那点上,古典的巫士“看见”这个,结论是因为意识的光芒随着集合点移动,知觉自然也自动集合在一起,由于集合点的位置不同,所产生的世界也就不会是我们的日常世界。 “集合点与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他说,“它属于明晰球体的一部分,而那是我们的能量化身。”集合点运动的结果是造成人类能量体形状的完全改变,不再是球或蛋形,他会变成像烟斗的形状,较尖的一端是集合点。如果集合点继续向外移动,最后明晰球体会变成一条细长的能量。 唐望说只有古代的巫士做到如此能量体拉长的境界,我问他在这种新的能量体中,巫士是否还是人类。 “当然他们还是人类,”他说,“但我想你希望知道的是,他们是否还是有理性、值得信任的人?嗯,不完全是。”“他们有什么地方不同?”“在于他们所关切的对象,人类的行为与欲望对他们已不具有意义,他们同时也有全新的外表。”......“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巫士,唐望?”“是的,我见过一个。”“他像什么?”“就外表而言,他像个普通人,不寻常的是他的行为。”“什么地方不寻常?”“我只能告诉你这个巫士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只说行为而已是一种误导,你要亲眼看到才能了解。”......“巫士故事中说由于他们能把形状拉长,他们同时也拉长了意识的存在时间,所以他们直到今天都仍活着,有许多故事是关于他们偶尔现身在世上的情形。”人类在能量球体时所知觉到的人类领域,是所有穿过球体的能量纤维。平常我们只知觉人类领域的千分之一。因此唐望认为古代巫士作为的优势便很明显,他们把自己延伸为球状长度的千倍,知觉到所有穿过那能量线体的能量纤维。 唐望在我的双肩中央拍我的背,力量猛烈到使我喘不过气,我以为我昏倒了,或者那拍击使我睡着了。突然间,我看见了,或者是我梦到我看见了超乎文字所能形容的事物,明亮的光线一条条地发之于一切,射向一切,这种光线从来不曾存在我的脑海之中。 集合点在睡眠时变得很容易移动。 意愿就是不带期望的期望,不带行动的行动(to wish without wishing,to do without doing)。 唐望说我们都有固定分量的基本能量,我们只能有那么多的分量,而我们把它全用在知觉及处理我们那吃人的世界。他再三强调,没有更多的能量可得,而且由于我们能用的能量都已有用途,以至于没有一点可用来进行任何不寻常的特异知觉,譬如说做梦。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问。 “我们该为自己搜刮能量,从任何可以找得到的地方。”他回答。 唐望解释说巫士有一套搜刮能量的方法,他们慧黠地重新分派他们的能量,去掉任何他们生命中虚浮的事物,他们称此为巫士的行径。基本上,唐望说巫士的行径是一连串应对这世界的行为选择,这些选择要比我们的社会所教导给我们的有智慧多了。这些巫士的选择是以改变我们对于生命的基本反应来重新整修我们的生命。 “那些基本反应是什么?”我问。 “面对生命有两种方式。”他说,“一种是向生命投降,包括屈服于生命的要求,或者反抗那些要求;另一种方式是根据我们的结构来重塑特定的生命形态。”“我们可以重塑自己的生命状态来配合我们的特定结构。”唐望坚持道,“做梦者能够如此,这是胡说八道吗?不见得,只要想想我们对自己了解得多么少。”“塑造生命状态是指塑造对于活着的觉察意识。透过塑造这些意识,我们可以得到足够的能量到达并维持能量体,而透过能量体,我们当然可以塑造我们生命的整个方向及结果。”(接近力量的第一步是创立梦。)创立梦意味着能对梦的一般状况有着精确与实际的控制。 “......今晚,在你的梦中,你要看到你的手。”开始时我在梦中寻找手的尝试真实惨不忍睹,经过好几个月的失败,我放弃尝试,向唐望抱怨这任务的荒谬。 (做梦)“一共有七道关口,”唐望回答说,“梦者必须要打开全部的七道关口,一次一道,......” 唐望说所有流动的能量都有入口和出口,而在做梦中,有七道入口,感觉上像是障碍,巫士称为做梦的七道关口。 “第一关是一道必须跨越的深沟,我们必须能够察觉一种在进入沉睡之前发生的特别感觉。”他说,“这种感觉像是一种舒适的沉重,使我们无法睁开双眼,当我们察觉自己正在进入梦乡,悬浮在黑暗与沉重时,我们便抵达了第一关。”我回到家,一连几个月的晚上都在睡前尽我所能的意愿察觉进入梦乡及在梦中看见我的手。任务的另一部分,有关说服自己我是个做梦者,达成了我的能量体,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有一天睡午觉,我梦见自己在看双手,这个震撼把我惊醒。结果这个梦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几个礼拜过去,我既无法察觉自己进入梦乡,也没有看见双手。但是,我开始注意到在梦中我都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事该做却记不起来,这种感觉变得非常强烈,因此我一个晚上会被弄醒好几次。 当我告诉唐望我尝试跨越做梦的第一关所遭遇的失败后,他给我一些指引。“要做梦者在梦中寻找某样特定的事物不过是一个借口。”他说,“真正的课题是察觉自己正在进入梦乡,但是很奇怪的,要靠命令去觉察是无法成功的,但靠维持住梦中的影像却反而能做到。”经过极大的努力,我真的在梦中找到双手,但他们从来不是我的手,他们只是看起来是在我身上,会变形状的手,有时会变得十分恐怖。不过我梦中的其他的事物都是很稳定的,我几乎可以维持住任何我集中注意力在上面的事物。 唐望认为自我重要感不仅是巫士的首要敌人,而且也是所有人类的敌人。 ......唐望的论点是我们的能量大部分是用在维持我们的重要感,这可以从我们永不停止地担心如何展现自己,担心是否有人崇拜、喜爱或承认我们中看出。如果我们能失去一些重要感,有两件惊人的事会发生:第一,我们的能量会从维持我们虚幻的伟大印象中解脱出来。第二,我们能有足够的能量进入第二注意力中,目击宇宙真正的伟大。 为了进化,人类必须先使意识从社会规范中解放自由,一旦意识自由后,意愿便会引导它走上新的进化之路。 “这些我都懂”唐望说,“你说的没错,你的毛病是把你的论点当成宇宙通用的。”“我们谈的都是基本的原理,”我叫道,“不管在宇宙什么地方都是通用的。”“不错,不错。”他沉着地说,“只要我们的集合点维持在习惯的位置上,你所说的便都是对的。但是当它被移动到某个界限之外时,我们的日常世界便不再有效,你所宝贝的这些原则也都不再具有同样的价值。你的错误是你忘了死亡拒绝者已经超越了这个界限上千次,傻瓜都可以明白租借者已不再受你我同样的束缚了。”"把意识当成实质的媒介是一项革命性的观念。"我敬畏的说。 “我没有说它是实质的媒介,”他更正我,“它是能量的媒介,你必须能如此区分。对于能‘看见’的巫士,意识是一道光芒,他们能把能量体附着在那光芒上,搭它的便车。”“实质的与能量的媒介有何差别?”我问。 “差别在实质的媒介是我们诠释系统中的一部分,而能量的媒介则不是。能量的媒介,像意识,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中,但是我们平常人知觉到实质的媒介,因为我们被教导这么做。巫士知觉能量的媒介也是同样的理由,他们被教导这么做。”唐望解释说,把意识当成我们环境中的一项元素来使用是巫术的精髓。在实际的应用上,巫术的目标是:首先,借着完美遵循巫士的行径,使我们已有的能量得到释放和自由。第二,利用这股能量,借着做梦来发展能量体。第三,利用意识作为环境中的媒介,以能量体及肉体进入其他的世界中。 “有两种进入其他世界的能量旅行,”他继续道,“一种是让意识来带引巫士的能量体到其他世界;另一种是巫士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使用意识为媒介进行旅行。你已经做到了第一种,第二种则需要极大的纪律和努力。”无机生物永远在搜寻意识与能量,如果你有可能两者都提供,你想它们会怎么做?站在对岸向你送飞吻吗?(摘录者语:灵魂出体大师门罗的《终极旅程》中也谈到了无机生物与有机生物有着不同的进化方式,必须互相远离才能避免毁灭。) “无机生物在算计着,”他说,“我可以感觉到。虽然我知道它们总在开始时设下陷阱,有效并永久地淘汰不适合的做梦者,但我并不感到欣慰。”他的语气如此急迫,我立刻向他保证我不会掉入任何陷阱的。 “你必须要认真的考虑到无机生物拥有惊人的手段,”他继续说,“它们知觉超人。和它们比起来,我们只是孩童,拥有很多能量的孩童,正是无机生物想要的。”无机生物有时候会物质化地出现在日常世界中,在我们眼前。不过大多数时候,它们以隐形的方式,以一种身体上的振动,像是一阵发自骨髓的寒战来显示它们的存在。 斥候是指陌生的能量,来自其他地方。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显现,但很不幸的是我们的意识过于忙碌,没时间去留意。然而在睡梦中,往来的道路便会打开,我们做梦,在梦中我们进行接触。 “你的意思是,无机生物像渔夫?”“一点也没错。在某个时刻,梦的使者会让你‘看见’被困在里面的人或其他的生物。”“无机生物无法强迫任何人留下来。”唐望继续说,要活在它们的世界中完全是自愿的决定,但它们能够借着满足我们的欲望、纵容我们来囚禁我们。要提防静止的知觉。静止的知觉寻求运动,它会创造投射来达成这目的。我告诉过你,这种投射是幻影。”我要唐望解释所谓的“虚幻的投射”,他说无机生物会钩取做梦者最深藏的感觉,无情的加以玩弄,它们会创造幻影来取悦或恐吓做梦者。他提醒我曾与其中一个幻影摔跤过,他说无机生物是极好的幻灯放映师,它们喜爱把自己像影片一样投射到墙上。 “无机生物在我们的世界中就像是投射到银幕上的影片。我可以说他们是穿过两个世界之间的稀薄能量的投射。”我承认那正是我的困境,不为别的,我想要知道活在那些隧道中的情况。(摘录者语:此处意为活在无机生物世界中) “我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困境,”唐望继续说,“而且没有人能帮助我,一旦你说出了要活在那世界中的意愿之后便无法悔改。为了要使你说出那意愿,无机生物将会满足你最秘密的欲望。”“它们的世界是封闭的,未经过它们的容许,没有人能进入或离开无机生物的世界。当你进入后,你唯一能做的事是表示要留下意愿,大声说出来表示造成一种无法逆转的能量波动。在古代,言语具有无可置疑的力量,现在不是如此,但在无机生物的领域中,言语仍然保有这种力量。”一群无机生物的集体意识先是诱使‘我’产生强烈的情感,‘我’大声而清楚地表明我的意愿:“我要把我的能量与那被困的斥候能量合而为一,帮助它自由。”无机生物于是致命地吸取了‘我’的能量体,然后那群无机生物的集体意识释放了蓝色的斥候,而把我囚禁,甚至‘我’的肉体也被传送到无机世界。(摘录者语:后来斥候带领唐望和他的弟子去找到作者,并把作者从无机世界中拉了回来,如果不是因为作者有多余的能量,否则已经死了。) 无机生物不追求女性,他们只要男性,无机生物是属于阴性的,而且整个宇宙在大致上是属于阴性的。“你能不能解释为何巫士必须使用无机生物世界的能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用的能量,为了能像巫士般移动集合点,需要极多的能量。”我提醒他自己说过的,为了能做梦,必须要重新分派使用能量。 “不错,”他回答,“为了能开始做梦,巫士需要重新界定他们的重点,节省他们的能量,但这种界定只是用来开始做梦。要进入其他领域、‘看见’能量、锻炼能量体等等,则是另外一回事。要做到这些,巫士需要大量陌生而黑暗的能量。”“但是他们如何从无机生物世界中取得这些能量?”“他们只需要进入那个世界中,我们这一系列巫士都必须这么做,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像你一样去做那么多蠢事。但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你这种怪癖。”唐望叫我回家去思索他所透露的事实。我有无数问题,但他不愿意听。 “所有的问题,你自己都可以回答。”他挥手向我告别。 唐望曾经给我关于回顾生命非常详细清楚的指示:要回忆起生命中的每一刻,重新活过所有的生命经验。他把生命经验回顾视为帮助做梦者重新分配安排能量的最大力量。 “回顾生命能使被囚禁的能量自由,若没有这种自由的能量,做梦是不可能的。”这是他的论点。 许多年前,唐望曾帮我制作一张长表,记载着我这一生中所有遇见过的人。他帮助我依序安排我的表格,以不同的活动来分类,例如我曾做过的职业、上过的学校。然后他照着表格引导我从从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重新经历了我与这些人的交往和接触。 他解释说回顾某次时间时,首先在心中安排好所有与要回顾的事有关的一切,这种安排是意味着一点一滴地重新架构起那次事件。先是回忆起与环境有关的细节,然后是参与的对象,然后是当事人自己的感觉。 唐望教我,回顾时要同时伴随着一种自然而有节奏的呼吸。在深深的呼气时,头要慢慢地由右转向左;而在深深吸气时,头从左转向右。他把这种头部的转动称为“扫描事件”,在心中从头到尾审视着所发生的经过,同时身体也扫描着所审视的一切。 唐望说古典的巫士,生命回顾的发明者,把呼吸看成一种赐予生命的神奇行为。因此也把它当成一种神奇的手段,用呼气排出所回顾事件遗留下来的陌生能量,用吸气来带回他们在时间发生时所失去的能量。 唐望表示,古代巫士对于生命回顾背后的解释是,他们相信在宇宙中有一股不可思议的销蚀性力量。这股力量借贷意识给有机物,因为赋予它们生命。这股力量同时也使有机生物死亡,收回借出的意识,而这意识被有机生物的生命经验所丰富。唐望解释说,古代巫士相信那股力量所追求的是我们的生命经验,因此非常重要的,那股力量会满足于我们生命经验的替代品,也就是生命的回顾。得到了它想要的,这股销蚀性力量便会给巫士自由,任他们去扩展知觉能力,探触时空的无穷尽。 “对生命的回顾永远没有终止,不管我们以前做得多么彻底。”“在巫士的观点中,宇宙是有许多层的,而能量体可以跨过这些层次。你知不知道古代的巫士今天在什么地方?在其他层次中,洋葱的另一层皮中。”在每个做梦的关口有两个阶段:首先是抵达那个关口,其次是通过那个关口。 做梦的第一道关口:是能察觉我们正在进入梦乡,或者梦到一场极为逼真的梦。一旦我们达到了关口,我们必须要能维持住梦中任何事物的影像,才能算是通过了第一关。 做梦的第二道关口:你会从一个梦中醒来进入另一个梦。你可以做你所能做的梦,越多越好,但必须能适当控制,不会在我们这个世界醒来。在通过第二关时,你必须更清醒有力地控制你的做梦注意力,踏实做梦者唯一的安全阀。一个完美的能量体拥有随意停止做梦注意力的控制力,这就是做梦者的安全阀。不管他们多放纵,在特定的时刻,他们的做梦注意力都必须带他们出来。 做梦的第三道关口:当你在梦中发现自己在注视着另一个在睡觉的人,结果发现那个人是你,你就抵达了做梦的第三道关口。梦见自己在睡觉表示你已经抵达了第三道关口。第二阶段是当你看到自己在睡觉时,立刻开始观察周围的事物。你开始刻意地使你的梦中现实与日常世界的现实融合为一,这个练习被巫士称为能量体的完全。两个世界的融合必须非常彻底,你需要比以往更为灵活流畅。 (摘录者语:难道做梦其实就是所谓的灵魂出体?前面两道关口的训练只是为了给出体做铺垫。之所以要一步步训练是因为需要积累能量和锻炼,否则没有足够的能量和经验来出体:例如会产生被无机世界永远囚禁的恶果。有部分普通人能出体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能量强度恰好支持出体。我认为唐望说的做梦不是指普通人“日有所思,也有所梦”般的做梦,而是指试图移动集合点的练习。请看下一段对话:) “关于这第二道关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很严重的问题,看个人的性格而定。如果我们倾向于放纵自己执着于事物或情况,我们就是在自找麻烦。”“怎么说?”“想象看,你已经体验到观察梦境的奇异快感,想象你自己从一个梦到另一个梦,注视一切,观察一切细节。如果放纵的自己的话,很容易就沉溺于致命的深渊中。”“难道身体或头脑不会自然停止吗?”“如果我们谈的是自然的睡眠状况就会自然停止,但这不是正常的状况,这是做梦。一个能通过第一关的梦者已经抵达了能量体,所以真正通过第二关的,从一个梦跳到另一个梦的,是能量体。”做梦的第四道关口:能量体要旅行到特定的、确实的地点。有三种方式使用这第四关:第一,旅行到这世界上某个特定地点。第二,旅行到这世界之外的某个特定地点。第三,旅行到只存在于他人意愿中的地点。唐望说最后一项是最困难与危险的,也是古代巫士最偏爱的。 日常世界对我们的控制在于我们的集合点被固定在一处时,知觉便成为一种完全决断的行为。日常世界对我们的控制在于我们的集合点被固定在它的位置之上,这种固定使我们对世界的知觉变得决断与强迫,我们无法逃避。如果我们想要打破这种完全决断的力量,我们只需要去驱散那迷雾,也就是说,用意愿来移动集合点。 唐望解释说我们(作者和唐望的一女性门徒)以全身进入了那世界,我们的集合点定着于无机生物实现选择的位置上,这种强烈的定着会产生雾状的感觉,使我们对过去世界的记忆变得模糊。唐望说这种僵化的自然结果是,就像古典巫士般,做梦者的集合点将无法回到习惯位置上。 “想想看,”唐望要求我们,“也许这正是我们在日常世界中的情况。我们被困在这里,集合点的定着如此强烈,我们都忘了我们是从何处而来,以及在这里的目的为何。”我们具破坏性,我们与世上所有生物为敌,因此我们没有朋友。



